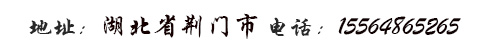人间有多少苦难,故林就有多少落叶钱利
|
点击图片上方蓝字“诗刊社”,一起玩耍吧^_^ 钱利娜,女,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离开》《我的丝竹是疼痛》《胡不归》《落叶志》。 我噤声 旧街巷和工业区有多少秘密 祖国就有多少湖泊沉默 每一个都幽蓝 如伤口。又似绷带 我噤声!角斗场上那块惊慌的红布是我 带血的犄角是我,插在背上摇晃的戟 甚至干枯了血迹的草坪,那扑向大地的 祷告者,也是我! 我噤声! 伤别赋 她念佛,恒河流在体内 她将在看见它之前失明,经年的关节炎 证明骨头还在,向她怒吼了一生的丈夫 所剩之日无多,飓风将停止 他没有哭过哭墙,拜过苦路。他猜测基督 长得像玉帝,在癌症部位念经、唱歌 她的耳朵适时地聋了,听不到他的咆哮 却被夜半的呻吟惊醒。唉,她不能 替他疼 她跪在梁山伯庙前,变薄的身体里 准备了全世界的宗教 ——她只剩下他了,请基督、佛祖、梁圣君 随便哪个神仙,让她领回两对翅膀 落叶志 向空山无数次投递简历的落叶 对着霓虹迷路的落叶 听夜虫点数客心的落叶 车间里覆盖断指的落叶 站在二十层高楼上 向秋风讨要工资的落叶 酒吧外伏在流莺脚下与之一起哭泣的落叶 同枝却分居半世的落叶 把棺盖上的颂词念给尘埃听的落叶 雁鸣中翻着史书的落叶,时代迷离 叶脉清晰 人间有多少苦难 故林就有多少落叶 甜 把毕生勇气 交给你眼角的一粒种子 和你一起失眠,听蝙蝠 彻夜扑腾翅膀 抚摸我吧,我身上的每一处遗址 一条苦行鱼 被你指尖的闪电救活 从深陷于湖水的眼睛 到开始松弛的每一道门 像抚摸容纳万物 却为几次后悔而变皱的丝绸 整夜拉着我的手吧 身体里飘落的樱花多了 流到心脏的血,在夜里 又凉了几分 唯一的孩子,睡在我们中间 他吃过彩虹、星光和我被蝙蝠弄伤的泪水 神舔了舔他后,说: 这孩子是甜的。我想 那一定是遗传你的 鸬鹚 湖面并不比一生广,绕不过的 不是边际,而是浩渺的内心 和她吐露的三重深影 它不是鹤。鸣叫而出的幻景清扫 日复一日的秋霜 也不是我,为不可及的乌托邦 消磨半生。候食的鸬鹚 离独坐半日的妓女有多远 差一部圣经,半个童年? 还仅在一壁之隔?若它搁置觅食之事 飞翔,就能越过 在掌心种植荆棘的官员 在麻将声里对骂的拆迁户 画出我想要的天空和伦理? 忘了它吧。即便从它歌唱的喙中 假想出一把大提琴,也无法安慰 丧失暴动的心。它把一切秩序都练熟了 机关的长廊。弗洛伊德的迷雾 俯瞰万千蚂蚁沸水中打滚的检察官 母性的河流。但每一个角色,都不像我 我在何处? 我是个弱者。面对只能低飞的鸬鹚 像面对另一个自己 充满了柔情 孤独者的五月 旷野春草茂盛,一对麻雀 从废弃的水管中飞出 凹陷又圆满的贞操 衔着泥草,忙碌而哀伤 那些空置之处,圆满处的缝隙 都可暂时为家。它们细碎的鸣叫 在飞,小小的阴影 认识我的每一个伤口,但我的伤口 独自旅行多年 没有一所房子 没有一个骑兵 开败的荷花,找到的每一个角度 都是消逝。薪火燃尽 与镜中每一对开始下垂的乳房 分享着孤独。对自我的封锁 已经多日,吃素、冥想 在失眠里把自己 想象成一滴露珠 我的缄默滚动,说与不说 也不能与彼岸靠得更近 不再对一只蜂 掏出胸怀已久的蜜 有多久了,我羞于说起爱情 像一头结痂的鹿羞于说起鞭子 在雨中,我胸前一万匹马释放于旷野 嘶鸣、眺望 奔跑吧,用雨水洗涤鬃毛 若我回望,有没有一把草料 可以成为我的故乡 在地平线消失之处 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骑兵,右手执鞭 左手向我捧出山茶花 持续的病历 拣一个僻静的园子 坐下来,损耗一棵树的 是经年的虫子 还是瞬时的花香 他叫桂树,开得正好 他会跟随一阵风 落下花与叶,像一场 又一场阵雨 在雨中,他是被隔远了的钟声 他是寺院,用一次相思 砌一个台阶 我坐在他身旁,不用相互递名片 不用像一个外交官,把每一词语 熨得整齐,滴水不漏 也不用变成一只妖蛾子,飞舞、炫技 “身体便是天梯”,不用为了取悦他的教条 攀爬他的花蕊。这持续的病历! 秋深了,我坐在桂树旁 不再登高望远 想着死亡是一场早就开始的旅行 若我流泪,他会落地为泥 并开出新的小花。有那么一刻 这满目金黄,点点滴滴 屠戮后的平静 仿佛全为了我 彼岸花 春天把一万种花朵递到火里 炼出一千种开放 它的暴力对每一朵花说,洗尽铅华 脱去华裳。但我的爱情 是被雨水弄坏的谷仓 是饱满的果园,架着无人的梯子 是弦上的手,忍住不发 所以秋天捎来爱人 美如虚妄。当他注视我 眼睛就开出彼岸花,火红的勾连 与明天的遗忘达成平衡 当他抚弄肩膀,叶子就落下来 当他亲吻,云纷纷退去,天空高远 当他进入一朵绽放的花朵 就会有一列绿皮火车 把喘息当作歌唱,忘记终点是恨 ——他多么厌倦铁轨,又忍不住夜夜敲打 这身体的味蕾和哲学! 他说,我们一拥抱 冬天就来临,你渴慕的枝上空无一物 每个伏在枝头哭泣的人,你都会以为 是另一个自己 现代生活 日复一日,我吟诗诵经的舌尖 与政府大楼不断上升的台阶 从两个方向和温度,消磨着 又一个清晨。呐喊吧,蒙克 扭曲的脸庞 安慰不了我骤雨未歇的屋宇 在我与尘世的接洽之路上 工匠忍辱的榫卯 已故去多日。钉子还在满世界喊疼 我流出的血却是沉默的。绵绵群山中 妇人的身体,是我。用旧的家具 也是我。在短暂的一刻,请让我 像遗忘的技艺一样美 温润、木质的身体里安装着一面镜子 “海棠太美 不宜让她长得太高。”黑暗对我有诸多评语 它驯服了一切,却无法驯服满天繁星 在我眼中找到宝石 娜夜·推荐语她如伤口,又似绷带的写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丰厚的创作准备、枝繁叶茂的意象、对生命经验的诗性处理、综合多种诗歌元素的能力,使她的诗像穿越幽暗隧洞的火车,冒着冷静的热气,且警笛尖利。她是一位具有沉思品格又感性丰盈的诗人。别让灵魂与生活对称 钱利娜 十余年写诗,西绪弗斯就是我。 巨人手中的巨石作为反抗现实的方式,在我手中有了独特的形态。它分行、短小、赢得的目光很少。它的美学枝繁叶茂,它的伦理潜隐,如石下清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诗歌看成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每首诗,反复用掉的是内心的回声和阴影,呈现的是灵魂与生活的不对称性。诗歌借助汉语的马车将我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对未来的张望连根拔起。在它繁复的根系,可以看见露珠与泥土、昆虫并置,过去与现在交织,这是我的诗歌渴望企及的灵魂风景画——准确并有延展性的细节,十分复杂的理智与情感,以及对现实形而上的抽象。抽象,是炽烈后的寂静与空灵。当我们说起往事与历史,事件已经死去,只有诗歌完成了承继和重复,并在隐喻中复活。最初,诗的圆心是“我”,孤独的分泌物,自我的心理控制,她的原始性与河畔纤夫的劳动号子、高山上的两性对唱、与神通灵的咒语同宗同源。生活总是缺了一角,我把这种个体经验看成是一种普遍存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底层,每颗心有每颗心的底层。缺失的一角以及由此滋生的爱恨是我们共同的遗传基因。精神基因造成了我灵魂的形状——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它超过生活的那部分锯齿形面积,就是我的诗歌地图。在忧伤中歌唱,是诗者在地图上的交通方式,她的另一种呼吸。正是这种洗涤与呼吸使我获得不断更新的活力。 回到诗中,只有语言能抚慰这种哭泣。诗歌的本质是语言,一个语言的瘾君子,渴望在文字的炼金术中寻找到迷人的多义性。近年来,我用复杂性的追求是对诗歌结构的威胁和挑战,我所面临的是,胃里的沙子如何变成珍珠?于是,暧昧与曲折、缠绕与释放、对古典文学的鞠躬与现代意识的杂糅,成为喂养我诗歌写作的海浪。而语言也将用两种高度满足自己,一是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创程度,一是文本揭示生命体验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当深沉的智性包围着我,追求美学化的心灵密语仍然是我顽固的梦。同时保持住丰沛的理性经验和潜隐的激情,那是诗歌张力的源泉。对异质的追求考验着天赋和训练。一个好的诗人,就是写醉鬼,也能写出他的时代感和悲怆。这是我对优秀诗人的界定。 “这世界没有结论(狄金森语)”,只有诗歌伫立远方。在我与诗神通灵的过程中,我总是发现自己的有限性,这让诗歌写作,很像灵魂无穷的冒险。正是这种冒险,远远超过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来源:《诗刊》年12月号上半月刊“永定土楼·第31届青春诗会专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huaa.com/schhy/4270.html
- 上一篇文章: 梦想若是一朵花昨夜压轴亮相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