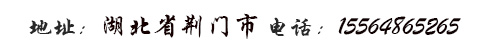艰辛与磨难酿造客家山歌
| 说粤东北的梅州是“文化之乡”,也许有人会心存狐疑,如果去一趟梅州,在城区里仔细考察一番,一定会打消疑惑。那里有看不够、听不完、离不开的文化魅力。岭南音乐文化中客家音乐是最为丰富且性格鲜明的一支。想要了解岭南音乐,梅州是不可或缺的。去梅州听山歌是我的一大情结和乐趣,也是一项文化任务。攀桂坊——文物由来第一流我坐深夜的航班,乘着月色登机,未及喝完一杯水的功夫便被乘务员催促下飞机。半夜里,山城的风有点甜味。梅州,历史可溯自二千年前。据说城东有一棵千年古梅,隆冬时节一树梅花天地春,客家人好梅,视为至爱和知音,故曰梅州。叶剑英元帅诗云:“心如铁石总温柔,玉骨珊珊几世修;漫吟罗浮证仙迹,梅花端的种梅州。”叶帅文武双全固然是近代客家人的骄傲,但如果要细数客家的先贤名人,实在是不胜枚举,光一个攀桂坊就令人惊叹不已。我在梅江边漫步时,发现一座“状元桥”,这必定是出状元的地方。果然,这一带便是梅州的“风水宝地”。旁边有著名的东山书院、东山中学、大学校长博物馆、达夫楼、将军楼等。怪不得郭沫若为此感慨:文物由来第一流。如今,这里被打造为客家公园和中国客家博物馆。客家博物馆公园内建筑很气派,最为瞩目的是广场上的多尊以客家母亲为主题的雕像,很有人文份量。我所知,客家人的传奇大多就是客家母亲写就。思忖间,便到了远归桥。经过远归桥才是最值得走走看看的、梅州最具人文厚度的攀桂坊,坐落在周溪(以大儒周敦颐命名)和梅江环绕的方圆几公里的半岛内。坊内分布着难以数计的名人故居。“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黄遵宪的纪念馆——人境庐首先进入人们的眼帘。此为公度先生晚年蛰居的地方,“人境庐”寓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内有很多先生遗下的文物、著作,以及后人的纪念文书和相关历史记载。移步隔壁,则有恩元第和荣禄第,属于纪念馆的组成部分,都是客家人进士入第的、功成名就者的象征。如今被开辟为梅州非遗文化展览馆,两层小楼布置得很精致,有小天井和回廊连通各个展览区域。逛一圈就能了解从汉剧、山歌、民俗艺术,到客家美食等洋洋大观的四百多种各级非遗项目。漫步攀桂坊的街巷,仿佛一趟对客家民居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精神巡礼。往南边江岸有黄药眠故居,接着是谢发、李仲昭和张简荪的故居,往北往西深入小巷内,则有杨雪如的故居(双魁第)、杨问渠的故居(资政第)、李黼平的祖居(大史第),还有黄伯韬、张资平、李国豪等名人故居。当然,我最感兴趣的是张棣昌故居(敦本堂)。张棣昌,很多年轻的乐人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他算是客籍最有成就的音乐家,广东音乐家协会的首任主席。他是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开拓者,传唱甚广的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便是张先生的代表作。山茶花——客家山歌特出名若说攀桂坊的学人追求的是庙堂之高,而山中与梅花同在的客家宝贝便是山歌了。有诗人说,梅花是客家人的乡愁。如是,牵引客家人乡愁的无疑就是“特出名”的乡音——山歌。有音乐的城市总是令人羡慕,有山歌的乡间同样令人向往。只是我们对于音乐的现代文化追求不自觉地倾向于前者,似乎山歌在乡间逐渐消逝,走入博物馆成为不可挽回的宿命。尽管这样,我从情感到理智,都有某种不甘和隐痛。一大早,我前往梅州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可爱的小刘老师带我参观了成果展示,兴趣浓处我们还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小刘是本地客家妹子,唱得好。我们的歌声惊动了刚刚完会的山歌剧传承人滕冬红老师,他耐心给我们科普了客家山歌的艺术特点和介绍了自己的山歌剧创作。话语间发现,山歌剧更为他们所看重。山歌剧被称作“美丽的山茶花”,近年在他们的努力下取得骄人的成绩。我饶有兴味地跟着小刘老师专门参观他们的“山歌剧团历史、优秀成果展览”和山歌剧场,也为他们作出的努力而感动。前不久,听闻著名山歌艺术家、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仙逝的消息。黄婉秋的祖籍就是梅县的隆文镇。《刘三姐》的故事似乎与梅州的刘三妹传说有关,对比着仔细听听,原来壮乡与梅乡的山歌渊源千丝万缕。汉乐故里——钟灵毓秀多名人有学习音乐的年轻朋友问我:汉乐是指汉族音乐吗?我一时语塞,不置可否。作为一个乐种却冠以“广东”之名,其故里竟是离开梅州近公里、处于粤赣闽边界的隐秘小城——大埔,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翌日,为探寻广东汉乐的起源地,我请当地的出租车朋友带我一程。与司机朋友一路聊的是他们家乡松口的山歌,他谦虚说不会唱,但说起山歌却是一套一套的,我想他是不屑于在我面前“亮剑”吧。很快我们就来到大埔博物馆,其与汉乐保护中心、翰林山歌剧院是连体建筑。周日,没有预约当然就有可能吃闭门羹。我一心想看看汉乐在发源地是怎么样的生存状态,听听这古老的“宫廷雅乐”在大埔是怎么个“雅”法?意料之中的是,没碰上音乐演出,只看到西湖公园中的汉乐演出舞台,想必在这里的演出是常态。意料之外的是遇到翰林剧院有新山歌的录音。不便打扰,我在后排静静聆听,大约是唱大埔的自然风光和美好生活,用的就是《客家山歌特出名》的调子。才几句的山歌磨了半天,老师对演员的要求极为严格,也可以理解为山歌要唱好是很不容易的。录音的间隙与他们攀谈,他们也表示,汉乐发源地很难找到具体的地点。回想在梅州时滕老师说,汉乐是因为当地在朝廷做大官的人退休(或者被贬谪)回到乡里居住,顺便将汉乐带回大埔。于是,这个乐种便在此生根、发芽、成长起来。出了西湖公园驱车出县城,准备去李光耀故居。路边有一块形似印玺的巨石,司机突然停车向我说起这块石头的神奇来历。神奇传说是乡村文化的固有内容,听听就好,而大埔县的现实传奇却是名人辈出。县域常住户籍人口33.14万,居民竟有26个民族。海外华侨、华人达5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之乡,这在旧时交通十分闭塞、山中之山的大埔,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奇迹。还有“父子进士”(饶相、饶与龄),“一腹三翰林”(杨缵绪、杨黼时、杨演时),“兄弟三将军”(范汉杰、范剑江、范作人),“四位省主席”(罗卓英、吴奇伟、范汉杰、赵公武)和“一门二总理”(李光耀、李显龙)等成为美谈。大埔的名人故居星罗棋布,顶级大咖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是客家人的骄傲。我们沿梅江在三河坝转而顺韩江南行,不久就到达田家炳的故乡和李光耀的祖居地,相距仅几里路。跟在城里不一样,乡村一般都坐落在山坳,或在河边,田家炳和李光耀的家乡都是一姓村庄,在韩江上游一处非常开阔的河岸。村庄里遇见当地的老人家,问起田家、李家,都有一些传奇故事。看他们的祖居却是与四邻无异,旧民居多为低矮的土砖房,基本上都被废弃或者消失了。如今见到的都是小楼房,承袭老一辈的传统,都给镶上一个“第”“府”之类的屋匾,可见读书进仕、光宗耀祖是这里人的进取精神。李光耀的曾祖父在南洋赚了点钱便急着回来捐了一个小官,就是这种文化使然。之所以说客家文化自成体系,是因为其内容丰富而又独具魅力。其中音乐文化就有客家山歌、山歌剧、汉乐和汉剧四大板块,实在是令人称羡,凭此无疑是可以傲居地域文化之高处的。在广州,客家山歌偶尔在白云山的广场上响起,也常登上音乐厅的舞台和荧屏,可是怎么听都没有张振坤、汤明哲他们那一代人在山间所唱的那样悠扬动听,有味道。而这味道,可能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山里的人的艰辛、磨难酿造出来的。尽管在客家人的歌声中极少透出悲情,而是一种无从选择的乐天和达观、一种幽默与智慧,但是,听到深处,仍然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愫隐藏在其中。山歌嘛,自然是山里人唱得好,也是在山里听得舒服,像野风吹拂,像山茶花的清香,像挂在山间的月色,特别清澈。麦琼文/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huaa.com/schxt/11931.html
- 上一篇文章: 花好月圆,家团圆,红红火火过大年
- 下一篇文章: 节令之美小寒丨6日小寒风信报梅开,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