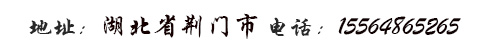一个人和一座园漫谈乌普萨拉植物园中
|
设计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www.gdgoran.org/fengshang/chaoliu/1294.html 上篇聊了聊乌普萨拉植物园的概况,中篇更想聊一聊我和这座植物园的一些故事。 留过学的朋友大概能理解,留学期间的空闲时间通常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由于文化差异,不是每一个中国学生都能适应西方的社交方式和西方青年群体的普遍爱好——至少我并不能接受那些嘈杂的聚会,蹦迪或者冷餐会,我也并不太喜欢那种我始终得保持分认真才能跟上的英文休闲聊天。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国学生中,也极少有和我一样对探索自然抱持着高度热情的人,出去看个鸟,拍个花,哪怕是聊聊共同爱好,也会成为意见比较奢侈的事情。 这种社交状况说不上健康,甚至是有点偏执的成分在里头,但我始终还是希望能够让本不那么令人开心的空闲时间至少变得自由一些。于是,自己一个人逛植物园就成了一个好的选择。现在回过神来再思考它之于我的意义,甚至就如田园归隐之于陶渊明的意义一般:时看时新的植物们总不会让我空手而归,而更重要的是,在快门声声之中,我也可以暂时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享受暂时的随性与自由,以及切切实实的收获感。 既然咬定这块自留地不放松,自然也要跟着它走过一个又一个月,一个又一个季节。秋季是每个学年开始的季节,也照理成了我刷花之旅的开始。乌村的夏末至深秋的变化仿佛就在恍惚之间:不落的白夜不知何时慢慢变短;阔叶树林突然开始变得鲜艳,然后落叶满地...... 秋季,植物园的不少球根植物会在这个季节开放。在课后和周末花点时间稍微转一转园子,也能有一些收获——不少秋花球根植物都算是很有名气的,比如传说中以秋水仙素在高中生物书中走红的秋水仙(Colchicum),就是其中的一员。 图中的秋水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杂交种:阿格里皮娜秋水仙(Colchicumxagrippinum),这种爆棚般的花量真是让人感到惊讶..... 一种没定种的秋花番红花(Crocussp.)。它的上方正巧有一棵葡萄科的落叶藤本,秋天一到,它便很自然地从鲜艳的落叶堆里探出头来。 一些仙客来属(Cyclamen)植物也会在秋季开花,比如图中的常春藤叶仙客来(Cyclamenhederifolium),就零散地分布在植物园的各个角落里。 说到常春藤,另一种和常春藤有关的植物:常春藤列当(Orobanchehederae)也在这个季节开花。欧洲人对于寄生植物的看法似乎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不仅在欧洲的植物园里看到列当,齿鳞草和野菰的引种栽培,甚至还听说在花市里有寄生植物的种子贩卖...... 但无论如何,如果说春季和夏季总是北欧生命的盛会,而秋天就好像是在狂欢之后慢慢收拾房间里的陈设,等待漫长而安静的冬季的过程——自然,我刷花的心境是总不及春夏那么充满激情。所以我每次只是随便走走,看看哪些秋花有点意思,就稍微随着性子拍一拍,并稍微有些恐惧和无奈地等待着冬季的来临。 气温进一步降低,白昼的时长也越来越局促。深秋之后便即将是漫长的冬季。这株北美金缕梅(Hamamelisvirginiana)应该是19年的冬天来临之前,我最后在瑞典室外见到的花了。 告别金缕梅之后,就是北欧的冬季了。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冬天在户外见不到一朵花的情况。哪怕是在长沙最冷的时节里,也能看点山茶蜡梅聊以自慰。自然就更不用提四季花开的岭南了——冬季正是红花羊蹄甲满街盛放的季节。 但北国的户外只有白雪或冷雨,堆积或坠落在枯黄的草地,掉光叶子的落叶树或者那些还在坚持着的裸子植物身上。我的学姐曾用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来形容这番惨状:冬季进到林子里,放眼望过去看起来活着的东西不超过五种。从这个角度出发,也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瑞典地衣分类做得如此精细了——除了深厚的博物学积淀之外,大概也和它们冬季依然健在有着紧密的关系吧...... 但万幸的是,人类早就发明了温室这种东西,来跨越气候对于植物栽培造成的阻碍。理所应当,这座小小的温室也成了我冬季难得的精神寄托,每次想刷花了,或者单纯是觉得抑郁,无事可干的时候,它总可以是一个可选的温柔乡。 (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介绍乌村植物园温室的文章:观感良好的热带植物小温室可以是怎样的——乌普萨拉热带植物温室#北地的断笔01,但这篇文章其实写于我来到瑞典的早期,自然也无法提到冬季里它那种无可取代的特殊性。) 大彗星兰(Angraecumsesquipedale)就是在冬季温室里开花的。这种植物在演化生物学研究史上非常著名:大彗星兰的花后部有着一根长长的距,是用于储存花蜜的器官。而达尔文老爷子在见到这种植物时,就曾预言一定存在一种嘴很长的动物为其传粉。而那种口器格外长的传粉者:马岛长喙天蛾(Xanthopanmorganii)则在达尔文去世21年之后才被人发现并描述。 让人感到更加兴奋的是,温室有时候会安排类似于特展之类的小活动:园方偶尔会将后备温室中正在开花的植物放在正式展区做临时展览,这其中自然不乏平时难得一见的珍稀植物。 临时特展的小展区,其中高密度地放置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植物。 特展中展出的欧洲原生兰花,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是:意大利红门兰(Orchisitalica);四斑红门兰(Orchisquadripunctata);叶蜂兰(Ophrystenthredinifera),镜蜂兰(Orchisspeculum);隐秘长药兰(Serapiasneglecta);二叶怒江兰(Gennariadiphylla)。 冬去春来,一株雪滴花(Galanthusnivalis)从植物园的角落里悄然绽放,这意味着自去年十一月以来的宛若肃杀般的无花季节已经悄然结束。那天是年的2月26日——尽管瑞典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但总是比无尽的荒芜多了一些希望。 那天我甚至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瑞典似乎很喜欢把帚石南(Callunavulgaris)当作盆栽种到各种各样的地方,而它们似乎又能在整个冬天保持着要开不开的粉色花序。所以也不难理解,这样不干不脆的的植物大概很难被我视作“冬季里开放的花”...... 欧洲常有把球根植物混播在草坪上的习惯,图中这丛雪滴花就生长在植物园的草坪上。雪滴花也是我在瑞典的一大遗憾。我总是想拍好这种植物,却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可恶的是,大部分原因就是懒),却终究没能在离开瑞典前获得一张真正满意的照片。 植物园的草坪和种植区播种了一些早春开花的植物。尽管它们的数量算不上庞大,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出现总是让人感到释然——一种植物爱好者总算可以开始一年户外刷花的那种轻松感,真是太棒了 侧金盏花(Adonisamurensis)是东亚有名的早春开花植物,植物园有几处引种。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有这种植物的分布。不难想象,这种金色的花朵在尚且盖着雪的森林中绽放的样子一定非常震撼。 铁筷子属(Helleborus)是近几年开始热门的早春开花园艺植物,这个属大部分种类都分布在欧洲。图中是植物园栽种的圆叶铁筷子(Helleboruscyclophyllus)。 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白头翁属(Pulsatilla)植物一定是早春不可少的山地野花。植物园里收藏了好几种欧洲产的白头翁。这里放了两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种类:其一是海勒白头翁tauricola亚种(Pulsatillahallerissp.tauricola),其花外侧和花柄均被有银色的长毛。(这个植物现在已经被移入欧银莲属Anemone)。其二则似乎是一棵自播到旁边的海勒白头翁stryriaca亚种,在长焦镜头下展现出了媲美原生境的神奇照片。 春天的进程向前推进,植物园里的花也越来越多——如果说早春是迈入宴会厅前的长长走廊,四处装潢华丽却人影寥寥。那么中春和晚春就像是走廊尽头推开门后的正厅,一时间厅内人来人往,觥筹交错。在这样盛大的春意面前拍花,我所持有的心态不再是秋季那般整理陈设般的平静,吵闹而磅礴的生命脉动足以将所有的不愉悦淹没,冲走。 春天不能没有杜鹃。园艺基础+气候条件使得杜鹃花科植物早已成为了欧洲常见的园林景观植物,图中分别为植物园里的马醉木(Pierisjaponica)和屋久岛杜鹃(Rhododendronyakushimanum)。惊叹之余,我也不免稍感遗憾——中国作为杜鹃花科植物的的分布中心,原生杜鹃花科在园林上的应用却显得有些局限。我十分期待能在国内的街头巷尾,见到越来越多除了锦绣杜鹃之外的本土杜鹃。 某日在植物园里闲逛,却偶然在林下找到了一小片传说中的五福花(Adoxamoschatellina)。从生长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园方刻意栽种的植株。 大园区的墙根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沿着墙栽种了一大堆春天开花的小型草本植物。比如图中这个怎么也调不出个正常色彩的荷青花(Hylomeconjaponica)。 如果说对我来说,亚洲,非洲和美洲算是苦苣苔科植物的正常原产地的话。那么原生于欧洲的苦苣苔就是怎么看怎么觉得怪的存在了。图中为产自欧洲的喉凸苣苔(Haberlearhodopensis)的一个园艺品种。 北欧的晚春到夏似乎没有特别明确的接缝,植物园今年的宴会也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奇怪植物也在逐渐变长的日照和逐渐上升的气温里第次开放,将宴会的节奏一点点推向高潮。 夏天毫无疑问是北欧最好的季节:我不必担心是否因为刷花过晚导致太阳落山,光线变差。毕竟天空一直晴朗而明亮,那番下午三四点一样的太阳可以挂到夜里九十点才算偃旗息鼓。虽然植物园是开不到那个点的,但那种随性刷花的感受却非常畅快,是那种不会被孤独感所裹挟包夹的畅快——当然,如果不必想着晚上还要回家做饭吃饭洗碗这种事就更好了。 也许欧洲白睡莲的开花可以作为入夏的一个节点。植物园内不起眼的水生区中引种了原产瑞典的红花型欧洲白睡莲(Nymphaeaalba),也算是瑞典的植物宝贝之一了。 欧洲七叶树(Aesculushippocastanum)的开花似乎可以作为另一个入夏的参考节点。 夏天也进入了高原植物的花期。大概是因为气候条件过于可怕的原因,我怎么也没想到能在植物园里见到传说中的水黄(Rheumalexandrae)。这可是原产地在滇西北高原湿地的玩意啊! 除了高原植物,夏天还能见到一些更加神奇的种类。比如传说中的昆栏树(Trochodendronaralioides)。自己一个科一个目,在我国只有台湾地区可见。 相比之下,在植物园见到杓兰属(Cypripedium)植物这件事就变得并没有那么难接受了。而且事后还听说这个貌似是个园艺杂交种,嫌弃之情更多了一层...... 夏天的狂欢终将在尔后的几个月里慢慢结束,又到了秋季那般收拾房间的时候了。自此,一年的植物园花季完成了一个轮回,我也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它的四季。 前面便提到过,乌村的植物园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地点,没有它,我很难想象无数个周末应该怎么度过,也大概会给平淡无奇的留学生活再增加一层浓重的无力感——这份感觉我偶尔是能体会到的:在19年那个逐渐变得萧条的秋季里,我曾一度刷花看鸟这件事感到无趣。最后是如何重回正轨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植物园大概帮到了许多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这刚刚过去的一年有余的时间里,世界不再如故,我也改变了许多。无论如何,我依然希望能用这篇不算精细的记录,写下过去我与这座植物园发生的点滴,也许能给某天造访乌普萨拉植物园的爱好者们提供些许帮助,也许能给某位与我一样的留学刷花人带来一点共鸣吧。 参考资料: 关于大彗星兰的故事: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huaa.com/schjz/7868.html
- 上一篇文章: 竹韵清音格律诗词53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