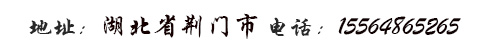游记一山有情,水有意,天地有大美
|
家门之外,即是世界。目力所及,皆成风景。 无论是飞往南半球的凯恩斯,还是在小区里看猫儿打架,都是行走路上的经历。关键是,走路的同时也请走心。 山有情,水有意。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心人会用脚丈量它的宽广,用发现美的眼睛去欣赏它的风情,用敏感的心领悟它的内蕴。 胡杨颂 胡杨树是一种与众不同,永远坚强挺立的树,在坐着吉普车领略沙漠之美后,我对胡杨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要大声歌颂它! 汽车在风尘仆仆的沙漠中行驶,放眼望去,只有三种颜色:蓝的天,黄的沙,黑的影,辽阔的大漠中有辽远的琴音,诡秘,苍茫,风到这里也会失去方向,阳光单调得可怕,四周金色的无边无际的海洋包围着我,大漠使杂欲归于宁息,轻纱飘扬的驼铃音若隐若现,在这里,我领略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美,心里感到十分寂寞。 我望着窗前的沙漠,心里感到无比不适应和沉闷。然而刹那间,我抬头看见了那排挺立的胡杨树,他们十分坚定,就算风吹得再猛烈也毫不动摇,胡杨柳是杨柳科中唯一能扎根戈壁沙漠的树种,耐干旱,而且生命力非常强,这种树,真是着实让我敬佩和赞赏! 秋天的胡杨确实很美,金黄的叶子,苍劲的树干,配上蓝天白云,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叶子黄的干脆,黄的一尘不染,黄的光彩照人,树干虬枝沧桑,千姿百态,能看到沙尘暴肆虐的痕迹,夕阳下,显得格外凄惨,我想:它的根是需要多么坚固,才能千年不朽?这大概是千百年的生长吧! “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是胡杨留下的永恒的传奇,胡杨树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它成为了“沙漠英雄树”,它,我想到了守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远离亲人和家乡,千里迢迢来到边疆,只为守护国土,他们身边没有依靠,所有的热血都化成坚挺的信念,他们都像胡杨树一样,他们的生命是永垂不朽的,就算死,那也是为国壮烈殉职,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精神是永远活着呢,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肩上扛着沉重的责任,他们展现了中国的顽强精神,谱写出了不屈的歌谣。 胡杨是坚忍不拔的树,它屹立在大漠中,坚挺着,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千年不朽。胡杨树是树中的榜样,边疆战士是全中国的榜样。 啊!胡杨树!我要大声赞美你! (陈涵怿) 山茶 冷艳争春喜灿然,山茶按谱甲于滇。树头万朵齐吞,残雪烧红半边天。——题记 五月,春色满园,小院花欲燃:玉兰惊讶满树,栀子花开清香满园,迎春花为春报信,杏花朵朵洁白,杜鹃千万朵盛放,万花争艳,繁花似锦。而院角的那颗山茶也静静地开放,它虽然没有楚楚动人的美,但却蕴含着春天的气息,给人带来开朗的心情。 眼前的这课山茶树干粗壮,浓郁如盖,仿佛是在成长的青少年;丰叶如幄,绿叶如黛,叶子如同上了油漆般油亮;山茶的香是清香,无药味,山茶的花是大红,艳而不娇,山茶的花瓣是柔软,细腻入微。这棵山茶默默无闻地开放,但微微摇摆的花朵又像是在炫耀它那勃勃的生命力。 它还没有凋零!我震惊。 上一次见到它,是同年的一月,寒风刺骨,整个小院沉寂着,只有这棵山茶迎着料峭的西北风傲然挺立着,绿得发黑的枝叶不曾飘落,而绿叶丛中已经探出了数十个小红点儿——花蕾,甚至有几个花骨朵按捺不住,竟在寒风中盛开了!“独放早春枝,与梅战风雪”,它们傲对风雪,凌寒自开,仿佛是在嘲笑我身上的羽绒大衣,我有些惊讶——原来世上除了梅,还有在严冬开放的花儿!但我又很不屑:它估计也像梅花,盛开一个月就急剧凋谢了吧!毕竟,寒风会给它的枝干带来伤害,它不可能开放长远的。 没想到,过了四个月,它还没有凋零,而是更积极地开放。“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陆游的诗句看来是真有其事了,我不禁为我对它的不屑感到惭愧。我静静地矗立在山茶面前,欣赏着它顽强的毅力与坚韧的品格。突然,我注意到它的枝干上挂着一个牌子。我凑上前去,上面写着:宁波市花——山茶。 是啊,山茶不就是宁波人的象征吗?宁波人靠海吃海,遇到大风大浪从不退缩,这不正是山茶那种顽强的毅力吗?宁波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闻名中外的宁波渔码头,这不就是山茶那种坚韧的品格吗?宁波人运用自己的智慧,用腌制的方法保存食物,宁波三臭令人赞不绝口,咸齑年糕汤百吃不厌,红膏呛蟹更是名扬中外,这不就是山茶花那种傲对风霜,雪中独秀——“老叶经寒壮年华,猩红点点雪中葩”的那种大智慧吗?宁波文化源远流长,靠得正是山茶这种默默无闻,但又不屈不挠的气节啊! 是的,山茶是极其普通平凡的,但我要赞美山茶,赞美与山茶一样的宁波人! (陆心怡) 海岛风情 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 白沙就静静地躺在海边,不远处,就是当地居民的小屋,漫步在主要的大路上,花便成了主角,不经意间,鼻子会捕捉到一丝幽淡的香,没有栀子花那样浓烈,也没有茶花的香味那样隐秘。那种香就这样自然,朴素地飘着,如同淡泊的诗。这时,你会发现路边,野生着当地的国花——鸡蛋花。在挺立的比人高的枝上,绿叶的掩映下米黄而渐白的花瓣温柔地展着。往往是这样,成簇成簇的白花在街旁将枝微微弯着,我想:这些花夜晚会变成照亮道路的灯笼吗? 这是个热带的小岛,越往高处走,就出现了热带雨林,高大的乔木或是灌木悄无声息地争占着空间,不时横出一些枝桠,当你的眼被这郁郁的丛林染绿时,就从林中传出不知名的鸟叫,在枝上也会开出细小、鲜红的小花,你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原生态的世界。几间草屋也在斑驳、深邃的林木间晃动。 这样泛有淡淡海味的安逸、自然的环境,滋养了朴实的居民。 虽说小岛没有与大陆相连,与众隔绝,但他们却有独特的审美,每家的园子中都植满花木,有路边的鸡蛋花,还有紫红的,如广玉兰的花成串地垂挂。有时,惊喜地发现几个小巧的金椰子平添生趣。城市里的人热衷于修剪树木拗造型,给自己园子装饰。其实,只需随意地植上几枝,就有一种活泼俏皮的参差美,当地的人便是这样做的。 寺庙是人们的信仰,不用钢筋,水泥,只需黑色的石块雕砌成,以花为纹,以佛为灵,就是这样,无奢华的虔诚。肃穆、清脆的竹片之音绕梁不绝,人们闲来无事便赤脚作祷告,专注地过着内心生活。这或许又要被讲究卫生的人嫌弃一番——总有观光者只看到他们“无所事事”的生活形态,却不曾去感受他们精神上的富足从容。 每个居民的门都敞开着,你若是需要什么,急着上厕所,他们都会理解你,无条件地为你提供方便。他们居住在被海包围的小岛上,过着“小国寡民”的简单和乐的生活,那种在“困”境里相互依存照顾的淳朴,已成为一种习惯。 城市里,大厦,车流,多么繁华,却又多么仓皇匆促,急功近利。而在这,清香、海风、雨林,花朵、寺庙、灵魂,简朴到贫乏,又富足堪比王侯。起码,我是这么想。 (孙宇飞) 上海风情 北纬31度,东经度,一个传奇。 她驻立在长江岸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黄金水道,经济腹地等等。 她便是上海,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十里洋场。 上海很老,像一个在混沌的夕阳里漫步的老人。 静安区有不少旧屋子,破旧、密集。除去那些拆不动的老房子,很多人认为应该拆掉这些房子,但最后还是没有去做。因为它们有时光,有岁月,有人活过的痕迹:墙角下随意摆放的那个陶罐,屋檐下晾晒的衣物,窗台上茁壮生长的盆栽……就像那些弄堂里靠着墙根坐在竹椅子上摇着蒲扇的老人。 如果你起得早,在油条和豆浆的香味还未飘满弄堂时,你就可以看到有无数的老人坐在弄堂口。不聊天,也不看报纸,就只是盯着路面,仿佛回忆着年轻的种种,等待着黑夜的到来。所以我小外婆总说上海人怀旧。 上海也很新,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旅人踏上新的征途。 在全国闻名的陆家嘴区,东方明珠像一帝王带领着身后的大臣,不断刷新着这一区域的天际线。它们的不断壮大就像是这里的年轻人。 视线下移,街道上年轻人衣上的名牌Logo反射出刺眼的金属光泽,红灯前的白领一脸的不耐烦,不时地抬手看一眼手表,偶尔看到初来者向路人打听地铁方向,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繁华之都啊。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那是因为环境给的压力太大,他们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站住脚跟。这大概也是他们不让你讨价还价,坐出租车还得坐满的原因吧。 也有人说上海人总有优越感,这不,去见个亲戚,开口就:“进城了啊!”弄得爸妈一脸尴尬。其实上海的历史使上海人骨子里就有股傲气:年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而建国后,上海的商品更是成了一种象征,天生的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印象中的上海仍停留在张爱玲笔下的风情万种的民国时代,可她却用拆不到的房屋和令人目眩的霓虹灯、笔立如林的摩天楼群告诉我:这也是上海,两个不同的世界交融起来的城市。 (张伊宁) 水 也许,南方人的细致是从七千年前河姆渡人选择种植水稻就生根的。水田作物,不比那边半坡人所种的粟,到底还是娇了些。 这与水的缘分也便这样结下了。沿着长江,播下了柔的种子。柔到青石黛瓦都略显青涩,柔到门前小溪都静静缓流,柔到溪中鲤鱼都不敢打挺,怕惊起水花——只是潜在水底,你追我赶。 一座城,一份时光。在这儿时光是慢的。 江南的雨下的勤,但缠缠绵绵永远是江南式的温柔。一把油纸伞,便足以挡住整个世界的风雨。你大可彳亍于青石板上,不疾也不徐,因这本来就是江南人的模样——宠辱不惊。此时的城,此时的楼,都像是蒙上了一层虚无缥缈的薄纱,这薄纱可是由千万根细线交织而成。不知是哪一位歌妓的手绢? 洗衣妇在河边蹲着捣衣。她们好像赴约似的,三五成群,吴侬软语,但声音很轻,依稀能感觉到升调降调中江南女子的婉约风采。要相信,家庭妇女也是爱美的。她们所清洗的衣服,没有大红大绿,只是蛋白的青,青花瓷的蓝,素雅、端庄。很难想象,平时忙于家务的她们身着正装后又是怎样的美人。 楼舍是傍水而建的。他们用墙角暗自滋生的幽幽青苔轻锁时光。一般的房屋是没有镂空花纹木雕的,只是一睹白墙,几片黛瓦便可寄托一生。小院里都有一口四方天井,砖缝之间横生出青色藤蔓,有顽强些的,硬是开出一朵小紫花。一汪清潭,映出明月和江南人的脸庞。家家户户的房子总是挨着的。门槛上是女人们的天地,台阶上则是男人们的天下。女人在门槛上绣花,男人们在台阶上嘬茶,聊天。薄扇轻摇,扇走了时光。 江南多水,自然多桥多船。桥大多都是弯的,清澈的湖水映出它的倒影。江南人认为圆是幸福美满的象征。船以乌篷船居多,坐不了几人,文人墨客一般在船中温酒作对,船夫则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一副船桨游天下。 有人说,江南人太闲,那是因为水赋予了他们一颗宁静的心。 有人说,江南人太懒,那是因为水教会了他们怎样诗意的栖居。 江南因水而美,因水而富,因水而荣。 江南人因水而清澈,因水而美丽,因水而优雅。 曾经为寻心中的江南,去过前童西塘乌镇周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江南,以水为魂。 (励睿婷) 蒙古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飞机缓缓在呼市降落,饱览了十几分钟美景的我早已迫不及待。 走出机场,来到了草原。草,茫茫地向四处扩散,似泼,似洒,似在倾倒。绿是狂野的,墨绿,深绿,甚至是褐绿色。那在绿色中穿梭的蔚蓝色的一条,是河,如透明的丝绸,缠绕在一块巨大的碧玉上。风,静静拂来,携着花的气息。 饭前的傍晚,是静的,如此的静,是天地都沉寂的静,以至于让人有些不安。我们手抓着羊肉,品着纯正的奶茶,望着无垠的碧野,无比惬意。蒙古同胞在蒙古包内为我们献歌,大家欢笑着,有些甚至跟唱起来,不论音调高低,不论音色好坏,不论音节长短,大家有兴致就开嗓,开怀。 饭后,夜幕深沉。偶尔传来远处马儿的嘶鸣,一入耳际,便觉得这是生命的演绎。一会儿,有了蹄声——是赶马人骑着马来了罢?出去,便震住了。群马在小路上彳亍,赶马人骑着摩托在后维持秩序,马群有条不紊,向北而行。马儿昂颈长嘶时,甚是雄浑,震煞了我的心灵,恐怕连群狼齐啸也比不上一马之嘶的震魂。 入夜,是篝火的晚会。简简单单的铁架,加上一堆小山似的可燃物与火种,便构成了晚会。大家围着篝火,尽情而唱,开怀而跳。除了背景音乐,没有主唱,没有指定的舞步,没有缠人的烦恼,没有成堆的工作,没有人之间的隔阂。大家心手相连,围圈而舞。笑容浮现在每个人的面上。听着豪迈的歌声,望着暗绿的草原和小山丘,闻着草原上特有的香气——不是花香,不是草香,而是牛羊粪的气息,一种原始而贞洁的气息。 送来清晨的,总是一缕微风。清爽的风使人的神经极度地放松,似与世尘无扰。睁开眼,浓绿的小山丘与草原尽收眼底。看着小丘,恍惚间似看见了一个蒙古小伙,手捧哈达,端着下马酒…… 蒙古在我国的版图上似哈达,略显修长那个,透过哈达,看到的是蒙古族同胞的热情,真挚与豪放,他们背后是无垠的草原碧绿的河蔚蓝的天。 为何要在他人面前做一个令他人满意的自己?我们为何要将自己的塑形权交给别人?为何要掩饰起真实的自己?豪放的展现又何妨? 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现在的拘束成了兀兀穷年时的一声叹息……. (杨宇琪) 蒙古的骏马 大巴在苍茫无边际的大草原中,沿着一条蜿蜒却平坦的小路疾行。这路,像一条长蛇,无阻地贯穿整个草原。坐在车内的我们仿佛望到一条条长而宽的绿波,有时又看到一条极路途的银蛇般的河道,与我们一起在茫茫世界中穿梭。但我们的眼睛精神着呢,为的是寻找那大片绿色中的几个极少见的黑的或白的动点。若靠近它们些,就能感到大地在微微颤抖,就能听见粗犷雄浑的嘶鸣——慷慨激昂,势不可挡,不免为绵延不尽的寂寞的草原平添几分豪迈,也为我们的心平添了几分豪气。 这是蒙古草原的骏马,草原上最为普遍的物种,也是最稀有的物种。 它们不像牛,敦厚老实,甘于平庸。也不像驴,一辈子沉浸于忧伤之中,但它也不像花儿一样,生得娇柔,天生艳丽。马是后天的俊才,蒙古的马,是桀骜不驯的战神,是奔腾的精灵,狂放那个,羁荡,一身不服天命的自强气概,都从被它们踩踏过的草地上留下的气息中流出来。 漫漫黑夜,静谧,忧伤钻入每个人的心里,望星空能感受到无限的惬意,想起古人,在此时此地所做下怀乡,念亲之诗,就开始悲了。但可幸的是,从遥远的它处,一阵脚步声随着呐喊与嘶鸣,由远及近,奔驰而来,傲气冲天,将我们从悲伤的情怀中打捞出来。 于是我渐渐把“马”和“蒙古人”联络在了一起。此时此刻,马已不再是一匹普通的马,难道我们就无法想到它的刚强,豪放,粗矿,一点儿也不像蒙古大草原上生活的人们?人与马,是这片草原上有共同灵气的生物,也不都继承了这片草原品质,这个大家族的品质吗? 所以蒙古的骏马,是令我无法忘却的,它再普通,再平凡,却终终背负着家族的使命,拥有着家族,草原的精神! (佚名) 东极风情 南极北极,我是没观赏过。但东极,我可是去玩过两三天的。 东极是位于中国大陆东端的一个岛群,四周被东海包围。那里,湛蓝的海水,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古朴的村落,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中。 我们来到一户当地的人家住下,简单的屋舍却打扫得非常干净。房东阿姨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什么时候看日出最美。什么时候看日落最好。呜呜的汽笛声一响,我马上跑了出去。原来,一艘艘红色的渔船在晚霞的辉映下回港了。绚丽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蓝得绿绿的海面上荡起层层金色的波澜,渔民们站在自家的渔船船头上,黝黑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船靠岸了,渔民伯伯一个箭步跳下船来,把一筐一筐的战利品搬到码头上。螃蟹,鱼被分类称量,鱼儿正在痛快地翕张着嘴巴,螃蟹想趁人不注意逃之夭夭,都不想被渔民伯伯用粗壮的手掌一下子就给抓了回来。 码头上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来看热闹,爸爸平时喜欢吃蟹,一问价格不禁大喜过望,岛上的价格是在宁波根本想不来的便宜!要知道,我们也去过很多作为观光地的海岛,很多岛上的渔民们都是坐地起价以高出市场三四倍的“景点价”卖给我们的啊。“这里的人真朴实啊!”妈妈由衷地感叹。 吃完天然鲜美的海鲜,看完落日。我们徜徉在落日的剩余光辉中,漫步回住处,房东阿姨热情地招呼了我们,拿出亲手做的冰镇绿豆汤为我们解暑,吹着凉爽的海风,我心里涌进阵阵暖流。 第二天清晨,我们再次来到岸边,昨晚那么多的渔船竟然一艘也没有了。空荡荡的码头,只有海浪拍打着背沿,勤劳的渔民们又一次出发了,希望他们夕阳西下时,又能满载而归,带来幸福富足的生活。 东极岛的海那么蓝,不像我们城市边的黄色海水,东极岛的天是那么蓝,不像我们城市里布满PM2.5的灰蒙天空。东极岛的人是那么淳朴,热情,不像城市里那些黑心商贩和冷漠的人们。东极岛的人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有蓝天一样透明的心灵,有晚霞一样火红的热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心与大海融为一体,他们与大海一起描绘出中国最东端海岛上最美的画卷。 (毛璟然) 仲夏的小城 蓝,清晰的蓝,如墨般被谁信手描绘在天空。大片大片的云朵像棉花糖,又像小女孩单纯的泡泡裙,一颦一笑里都有童话般的质感。这便是温切斯特——英格兰南部的小镇。 我们的营地学校位于郊区,一路上少有人迹。大巴车行进的途中,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座纯白的小洋房,掩映在仲夏浓厚的绿荫之中,仿佛是七个小矮人的小屋,弥漫着温馨的气息。小洋房有精美的门柱,遮一层轻纱的落地窗,深蓝色的门边挂着盛开的蝴蝶兰。我们未曾与小屋的主人谋面,却惊喜地发现自己得以窥见小镇静谧生活的一隅。虽然曾是英格兰的古都,但小镇住民并不多,只有镇中心稍显繁华。居民的住所,咖啡厅,糖果店,书店等都是恬淡清新的模样。亮橙、米白、天蓝、薄荷绿……走上住宅街,恍若梦中。大大小小的洋房层次栉比,竟有种不规则的美感。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窗户上各种鲜艳的三色堇和蝴蝶兰,朝外开放的笑脸明媚而又灿烂。 “吃”也是温切斯特之旅的主要项目之一,然而大不列颠人的美食实在是让我有些失望。比起中华菜系的“博大精深”,它们只算得上是好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然而还是会有一些温暖的瞬间让我对这类精致文艺的吃食心生敬仰。街角的咖啡店,一对青年男女坐在露天的咖啡桌前享用下午茶,三层塔的松饼,蛋糕,三明治,以及甜蜜的草莓奶昔和红茶。这一刻,精致的杯盏与茶匙不再是冰冷的瓷器,它们在午后的阳光里有了温度。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走在僻静的小巷,老奶奶幸福地舔着蛋筒冰激凌,我小心翼翼地屏住呼吸,怕打破了这易碎的宁静。一个棕发蓝眸的小男孩站在面包房门前,举着甜甜圈吃得一脸的巧克力酱。一个长发的女子温柔地为他拭去,他对着她调皮地笑弯了眼睛……在国内颇具市井气息的场景,大排档,油炸摊,便利店的小吃,铁板烧,火锅等,与这里的恬淡安静的氛围完全不同。我们在寻找热闹与富足,他们则是在追求简单与安宁。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是也拥有完全不同的街头特色。 温切斯特的人们,像这座小镇上方的云,干净,纯粹,坦率,富有活力和对事物天生而来的敏锐美感。而我有幸走进这座小镇,有幸与他们相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清新气息,最是让人流连忘返。 (骆欣雨) 辣椒与川人 初次来到四川,着实是吃了一惊。 对川菜的辣早有耳闻,但重庆人的无辣不欢,让我始料不及。一条街道从头到尾,凡是餐饮,无不辣味冲天,令人、外人敬而远之。正宗的重庆火锅加的辣椒更是多到夸张的地步,可谓是“满锅红”。不识辣者,在偌大的四川竟难找安身之处。 几天后,在四川的山间游玩。行走于苍翠的绿林间,竟偶遇了一片火红——山间的平地上,种满了火红的辣椒。植株不高,却结满条条辣椒,干旱的土地丝毫不妨碍它们的旺盛生长,炽热的阳光下,仿佛一团火焰,带着咄咄逼人的辣香,热情地燃烧着。在团团火焰中,隐藏着几朵绽放时的辣椒花。洁白的花瓣透露出淡淡的朴素之美,它默默地开着,想必没有人会去欣赏它吧,纵使偶然发现,又会有多少人会相信它竟是辣椒的花朵呢? 离开四川,回到宁波,竟发现川菜早已步入宁波人的生活。遍地开花的川菜馆中,食客源源不断,老板用地道的四川话组织着工作。而火红的辣椒,也早已不是四川的专利,就像它那如同星星之火般的小而亮的白花,燃遍了神州大地。 辣椒没有争奇斗艳的花朵,没有香甜可口的果实,绝对算不上美丽。但它的花朴素低调;它的果热情似火。当你在广大地域见到辣椒的身影时,你会觉得它们只是一种作物,一种调料吗?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与出众的适应力,是否也象征着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川人?当你见到片片辣椒地时,你是否会觉得它们红艳艳的热情,从某一层面上也象征了川人的热情豪放?当你见到团团火红间掺杂了几朵淡淡的辣椒花,你在惊叹之余又是否会想到它的朴素,低调也象征着川人的低调朴实吃苦耐劳? 辣椒,是四川的象征,更是川人坚强不屈,热情豪放,默默无闻的象征。 (佚名) 味道饺子 今早路过一家饺子馆,店内生意兴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使我想起陪伴我长大的饺子。 按中国人过年的惯例,每逢春节必吃饺子。饺子这类面食似乎是北方人的专利,简约大方,粗犷又不失柔和。无一例外的粗线条、大手笔,总给人以厚重感,吃着心里踏实。 而饺子作为面食之极品,更是在春节的舞台上演变出大量花哨的习俗。比如说,人们会在饺子馅里添加各种吉物,预示不同的——当然是美好的命运。没有人会去计较真正的结果,而是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吃饺子——过年的乐趣。 这,也许就是饺子“风靡”全国的原因吧。 在我们家,每逢过年必吃饺子。 两三年前,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就开始为春节大量“囤粮”。那时的厨房是外公的天下。早上起来,餐桌上闪着保鲜膜和面粉,水滴的光泽,清一色的白亮,甚至没有过年那种红红火火的气氛。那几乎不怎么用的搪瓷碗里挤满了剁碎的猪肉,小葱和芹菜。一大块揉好的面团晾在一边,外公对着面团发呆。 踮着脚进入那神圣的厨房,我搬把小板凳和外公面对面坐下,即使只是叙些闲话,也是极有趣的事情。外公不会说普通话,我也讲不了宁波话,但这些丝毫不妨碍我们的谈天,白花花的厨房,祖孙两其乐融融。 终于,经过三天的忙碌,我们迎来小年夜,过年的第一顿饺子宴。那晚家里总是格外热闹,尤其是厨房,虽然厨房只有外公一人,炖了一下午的鸡汤,倒入圆润而饱满的饺子,让饺子在油汪汪的鸡汤中翻滚,直到裹上一层扑鼻的香味。 就这样,每年的鸡汤饺子都在期盼的目光中被送上餐桌,又在惊喜的欢呼声中被掀开锅盖。每个人捧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饺子,大快朵颐,每个人的脸都被门上的大红春联映得喜气洋洋。 这两年吃饺子的机会少了,不知是因为外公要照顾刚出生的小表弟,还是爸妈单位到了年末总会格外忙碌。很多时候买的都是超市冷冻柜里的饺子,口味也很花哨,不像以前,只有鲜猪肉加芹菜小葱。鸡汤是不加了,过年吃饺子也不再那么积极,经常是匆匆蒸几个饺子当午饭,有时垫上几片白菜叶,有时呢,连白菜叶也没有了。 没有饺子的春节似乎也没啥变化,但是总给人感觉少了点什么。 初到宁外,在宁外吃的第一顿饭,我心血来潮地买了一碗饺子。味道并不算好,但至少比速冻饺子强多了。挑一个靠窗的位置慢慢咀嚼,水汽氤氲久久不散,像曾经面粉弥漫的厨房,白花花的一片。 尽管妈妈总是强调面食是北方人的专利,尽管她也无数次地提醒我不能多吃猪肉,但我还是那样近乎痴狂地爱着饺子。 因为饺子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味道。 (叶斯语) 锦年语文 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huaa.com/schzp/8011.html
- 上一篇文章: 全长公里宜宾这条新高速最新进度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